每個事件都值得深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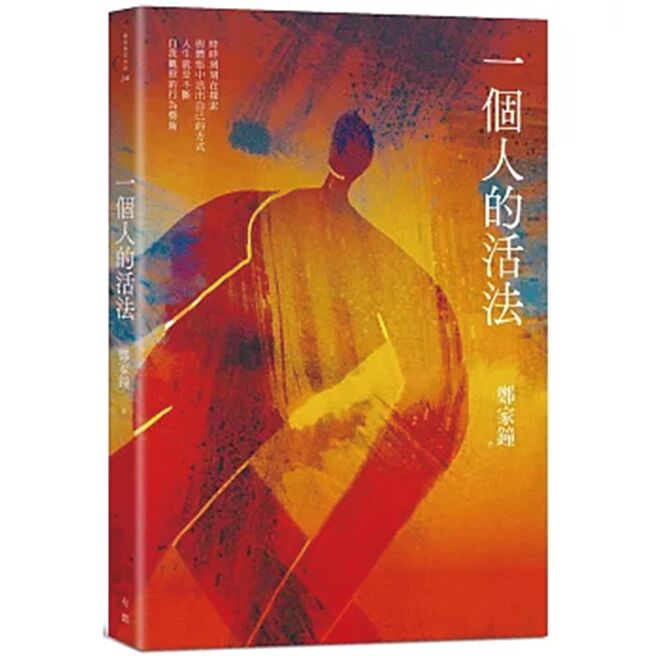
一個人的活法(有鹿文化)
2022年十一月在關渡美術館巧遇郭昭蘭老師。
她跟謝牧岐共同策展「在前衛外圍的莘莘學子:從1985年素描事件出發」。
這是怎樣的事件呢?其實是個美術系師生不想老是畫石膏像的事件,當時若干老師倡議素描不是臨摹石膏像練習,而應是自我觀照的藝術表現。這個倡議後來就枝繁葉茂成爲一個潮流。郭昭蘭把當年老師們的繪畫與裝置的作品,到學生們一系列的創作變化,及現在的學生如果回到那個事件的源頭─他們會如何創作?這些展品的呈現串接了北藝大由當年的素描革命,到持續演變的脈絡,一直到當下的再詮釋。
這成爲一個既前瞻又回顧的「事件展覽」,也呼應了關渡展「事件是一所學校」的主題。
郭昭蘭在策展說明中說:「素描事件對我而言,無不投射着雙重的青年形象:一方面是以藝術抱負投身剛結束鄉土運動的臺灣;另一方面則是相信單純藝術的實踐,便足以成就人生志業。莘莘學子的藝術自由與藝術理想性,已經是這裡每個師生兩代之間共同的橋樑。」
這意味着一個素描事件居然有這麼大的系列影響,甚至變成一個學校的學風資產,自然非常有意思。
有些事件只有回看,才能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在這個位置。
我也是被事件所影響纔會到今天的位置。
1970年的保釣運動,同時驚動了兩岸三地的青年。當時高中生的我,本來是丙組,準備跟大家一樣考醫學系,畢業後想當醫生的。
一直到某天受到保釣愛國熱潮影響,建中學生髮起罷課,在集體起鬨下各班班代表齊集圖書館商議罷課的後續,身爲班代的我也在其列。
當時處於戒嚴時期,罷工罷課形同造反,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更何況我們是在警備總部的鼻尖下鬧事?
迅即大批軍警包圍建中準備衝進來抓人,我們從窗戶望向門口,看到校長、老師與教官擋在門口理論,不讓軍警入校,這可是一種明顯的抵抗,同學們一方面事態嚴峻,一方面危及老師,於是班代表們終止罷課,呼籲同學解散回到教室,在關鍵時刻弭平了這場風波。
事後,教官來到圖書館慷慨激昂的演說,直指現在優秀同學不是想當醫生就要當工程師,文法組變成冷門組,想當年五四運動投入救亡圖存的都是文法科學生,同學如果愛國,應該要仿效五四,進入政治、社會、法律、經濟科系,別一窩蜂念甲丙組(工科及醫科)。
受到當時的刺激,一羣班代集體轉組到丁組,我也是其中之一。從此當不成醫生,最後當了記者。
保釣事件是個大事件,海內外風起雲涌,建中這個「罷課未遂」事件,是歷史洪流中的小插曲,但它確實影響我的一生,我當年的第一志願就是臺大經濟系,以爲「經濟」是「經世濟民」的縮寫(後來才知道是日本人將Economics翻譯成經濟的)。
我於是成爲經濟系學生,然後意外進入媒體。回看這段歷史,感覺到人生每個參與的事件都有它非比尋常的意義,原來,每個事件都值得深究,其與今天自己的位置息息相關。
我在這件事的學習是:
①此事促使我用三代以上的視角來看一些源頭性的事件。例如一羣同學的集體跳轉,有些人從政,有些經商,有些是律師或立法委員,註定也會成爲社會某些事件的源頭。
②再如臺灣的媒體發展史由戒嚴到解嚴,由壟斷到惡性競爭,由過去充當文化論戰旗手到現在深陷資訊操控的場景,三代的媒體人堅持了什麼?這堅持能傳承下去嗎?還有當前媒體人的價值觀轉變等,都因爲事件們的因緣和合而來。若要理解現況,我們需要理解「每個事件都值得深究」這個道理。
1985年的素描事件是教育事件,經過幾十年,總體的教育有提出什麼新方向嗎?有什麼事件可以推動教育轉型?尤其是AI時代?
一個運動起點是個小小事件,但一個事件變成一所學校,單純只是有人願意把它照料好發展下去而已。
因此,我對一個有意義的事件能夠踏出第一步,總是充滿了期待。(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