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博允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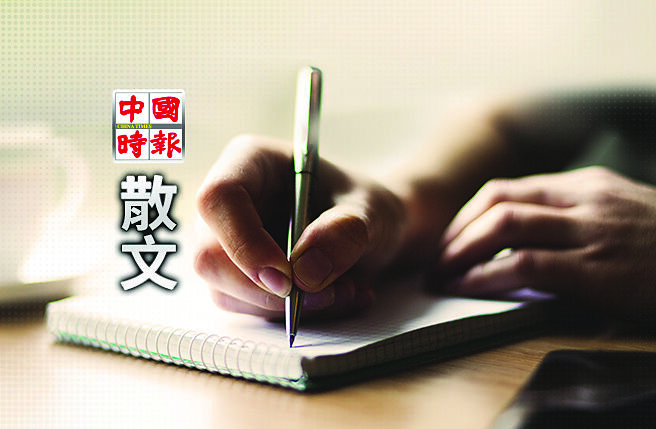
散文
許博允絕對是美男子。
然而他卻似乎沒把自己出衆的外貌放在心上,這是他的瀟灑,也確鑿地透露出他拓落不羈的藝術性格。在與他爲數不多的談話中,他講的都是關於藝術的事,不是手上正籌措的項目便是關於創作的態度。講起來總是興致高昂的,是一種我所熟悉的被某種創作靈感激發出來的興奮和喜悅的情緒。
第一次看到許博允是1982年在高雄舉辦的金馬獎上。那時我剛因自己拍攝的影片《異鄉女子》在金馬觀摩展放映而回臺。跟一羣演員明星坐在舉行頒獎旅館的咖啡座上聽老蓋仙夏元瑜教授說話兒。許博允風一般掠過我們桌旁,匆匆停下打個招呼,又風一般的走了。他一頭濃黑捲髮,落腮鬍。我當下還以爲是哪個武俠男星。
後來他和太太樊曼儂開創新象藝術中心,那裡的咖啡沙龍在八零年代的臺北,成爲衆藝文界人士聚會聊天的熱門去處。也是在那兒,經常碰見他。其實我們說不上熟稔,更從未有過深度的交談,大概因爲彼此的朋友跟對方很熟之故,所以見到面招呼起來彷彿就像熟朋友了。
在一個溫暖的夏夜,忘了是甚麼活動完後,大家鬧着要續攤,未料到最後只剩下我們兩人。許博允說肚子餓了要找消夜吃。應該是我開的車吧(那時我有一輛法國制的銀可可Peugeot)。我們在東區胡亂兜轉了一圈,最後他忽然決定要去找郭英聲。
真的嗎?已經十點多了啊。
但是許博允卻毫不遲疑,完全沒有顧慮地點着頭說:
就在逸仙路。
我就這麼傻傻的開過去了。如今仔細回想起來,彼時之所以行事如此不經大腦,推敲原因可能是我經常並不覺得自己是個女生,沒有隨時隨地提着女孩的意識和自覺。跟男性友人相處(尤其是對不來電或不可能成爲潛在男友者),更可以自然到彷彿是同性朋友似的。
話說那晚郭英聲和殷琪都在家。開門後便把我們迎進屋去。許博允和他們果然是熟透了的老友,主人完全不意外也不介意(或許這種夜晚突襲式的造訪並非第一次?)好像還特別理解似的,尤其殷琪,盈盈笑意一直掛在臉上,不曾撤下。
許博允一進去便問:有沒有泡麪?
殷琪說:已很久沒買了,不知還有沒有?
還好沒讓他失望,最後終於搜出一包來,馬上將之煮了。
他唏哩呼嚕將面吃完。記憶中好像主客彼此也沒再多聊些甚麼。就這樣,出得門來,許博允和我互道再見,各自回家安歇。
這真是一次伴隨些些無聊卻又特異的際遇。倒是我猜,在許博允的人生中大概不乏這樣的即興之舉,他渾身上下都是藝術家的滿不在乎、隨性和灑脫。也或許加上當時的社會氛圍,纔有那樣的即興之作吧。
回想臺灣的八零年代,各類革新、前衛思潮涌動,社會是蓬勃的,人心是燥動的。政治開放的呼聲與後殖民的反省聲浪波濤洶涌。女性的自我價值與解放,情慾、情色的風潮和實踐,更不用說本土意識擡頭與高漲。
活在那樣一種情緒高昂的社會氛圍中,心靈撞擊在所難免,猶記彼時我在混亂激盪的暗中躊躇,企圖摸索出一條自我的道途。
如今逝者已矣,一想到許博允,就無法不記起那個夏夜的奇遇。逸仙路上精緻的小公寓,黯淡的燈光,暗色的百葉窗。女主人身着水紅針織無袖短背心,她很瘦,燈影將她的笑容刻劃得深刻迷人。男主人長髮披肩,斯文中帶着叛逆,身形亦十分的削瘦。就這樣,在那個溫暖的夏夜裡,國父紀念館旁的小公寓中,突然被有着帥氣俠客外表的老友闖入,身邊跟着一個陌生好奇的女孩。他要了一碗麪吃完之後,便又匆匆離去。
之後我們互道晚安。他朝我擺擺手,我啓動引擎,看着他在公園闇昧婆娑的樹影下,一路消失在臺北暗夜的巷道中。(許博允先生告別式將於九月廿七日臺北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