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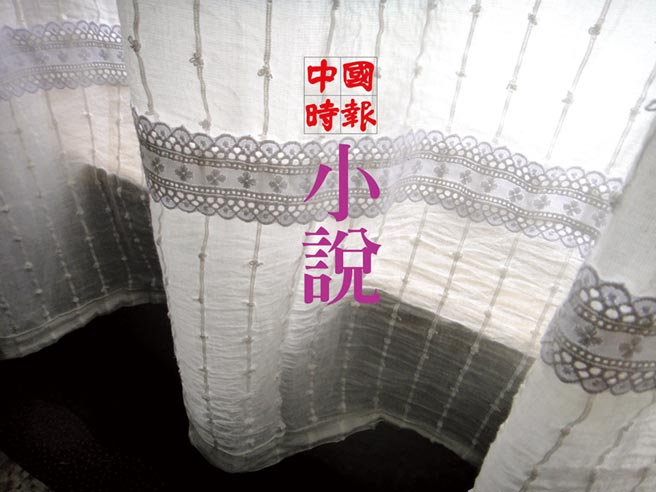
小說
如果咖啡具有形體,以現下的我而言,最喜愛的無非是帶着發酵酒香的日曬系咖啡,那宛如從電影《惡女花魁》萬花筒的斑斕絢麗之中走出的,穿戴美豔、一個眼神便能勾人心魄的藝妓。然而,心頭的另一側卻又極端的被豪爽、苦裡帶甘甜的美式所吸引,似是長滿大鬍子的大叔,在冷天裡以一老鏽口琴吹奏出的低沉音律。
話雖如此,好似對這黑色液體有什特殊堅持,卻也沒那麼堅持,喝到不合口的頂多輕扭眉心,配着餅乾麪包也就下腹了。
咖啡作爲飲品確實是一種癮,着迷那層次疊沓的風味與香氣;然而另一說是,飲品爲的是姿態的展現。然而姿態這事說來複雜,畢竟生而爲人,動輒大概都成姿態或風景吧?又有時喝者無心,觀者有意,連喝也要顧及他者的凝視實在疲憊,最終還是得回到自我本心。
如果咖啡是種姿態或風景,最不喜的約莫是那在宮庭風格,過度碧麗輝煌的建築物中,以浮誇花俏磁杯盛裝的咖啡。喜的則是西式老咖啡店裡,簡約白杯的黑咖啡,背景音樂最好爲爵士,與人們的交談聲錯織成一幅熱鬧的溫黃畫面;像是《咖啡與煙》Tom waits和Iggy pop所在的那種昏暗,不斷有光點流泄而下的,似酒吧的老咖啡館。
說起電影裡的咖啡,在心中久留不去的畫面竟都與殺機有關。一爲《色戒》裡湯唯在最終要與特務夥伴們打pass以示可以行動刺殺梁朝偉的咖啡店。湯唯俐落的米色風衣裡,一身孔雀藍旗袍,湖水色耳環,紫檀短跟高跟鞋,黑色短淺緣仕女帽,用轉盤電話聯絡夥伴後,回到位置上啜了一口咖啡。紅棕色脣印落在白瓷杯緣,鏡頭拉近,桌上僅喝了一口的咖啡與脣印,未動過的糖罐。而後湯唯拿出香水,在頸後與手腕緩緩的塗抹着,一時女性的軟香便充滿了畫面,雖然最後她香消玉殞了。
另一個時常縈繞在腦中的咖啡風景,則是冰天雪地之中,在木屋裡冒著白色煙氣的大壺黑咖啡。冷天喝熱咖啡絕對是能從心裡根部開始暖和的。《八惡人》中驛馬車站內,八人爲了活命各懷鬼胎的心計交鋒,終於有人在熱咖啡壺裡下了毒,中毒者將屋內嘔得滿是鮮血,引爆了最後的槍戰。
咖啡與殺機之間的關聯,也許是逐漸亢奮的腦神經、沸騰的血液。
比較認真地衝起手衝咖啡,是近幾年的事,到書店工作,與夥伴討論如何增加營收,剛好我們都喜歡咖啡。將水煮沸時,若店裡剛好僅有自己一人,便可以看着那些煙氣從壺嘴漫出,傾上一旁的大片玻璃,有時會無聊地用手指在煙氣上塗鴉,然後再看着那些圖案被仍然不斷涌出的白煙給覆過去,變得模糊,失卻輪廓,滑下幾顆水珠。
一切在煙裡的、如煙的,皆因朦朧而有美。
那於內在視域,如若從煙霧瀰漫浮現而出的一杯手衝咖啡,令人期待與着迷之處正在於它的曖昧與歧出,咖啡豆雖鋪墊了決大多數的香氣口感,然而溫度、水柱粗細、手法、器具皆會使氣味有着些微的不同。因此得到一包新豆子,有時如同得到一種新的色料般,期待它的質地變幻。
人生雖然無常,但生活較常摺疊的模樣爲抽取式衛生紙般的日復一日,在咖啡裡找點亂子又有何不可呢?
手衝喝多了,拿鐵便喝得少了,缺了圓滑的乳白,似變得愈發刁鑽而難以理解。許多時刻得到的迴應是:「喝咖啡有必要這麼複雜嗎?」、「有不一樣嗎?都差不多吧。」一下子就被話語隔到另一方,但其實並非追求名貴器具與豆子,僅是儘可能喝到屬於咖啡豆本身真實的氣味,不焦火,不調味的。
但在虛實相生的日子裡,真實難以澄明。生活的旋轉盤上,只能各取所好的飲取,流淌進體內的光影變化僅有自己知曉。
咖啡不語。
隨年紀增長,又久未與父母同住,才發現原來過往記憶中,向來嚴厲寡言的父親竟也喜愛手衝咖啡,此後這就成了我們之間幾乎唯一的共同話題。與父親過去諸多的扞格不睦,源於我們某部分的相似、皆不知如何扮演家庭角色,尋常親暱的父女關係,我們卻因彆扭而各自蜿蜒,在屬於自己的堡壘裡攻防。
那段總是喝即溶咖啡和商店咖啡的日子,無益的奶精與糖佔了絕大成分,但當偷偷摸摸拆開包裝,在杯中傾倒粉末與熱水,快速以小湯匙攪拌並喝盡,便達成了衝撞家中禁喝即溶咖啡和飲料的小小快感。
那不似拿鐵帶着圓潤的自然大地土褐色,不似單品豆的琥珀色,也絕非苦黑;而是一種不自然的、有點混濁的深褐色,經常表面還覆有一層霧白不化的奶精,像當時過不去的心緒,是生活裡小小的鬼魂般的事物;但卻喜歡看那些奶精在經過湯匙旋轉後,最終慢慢靜止下來,形成一個圖像的模樣。
現今很少喝即溶咖啡了,然而在某些時刻,體內的閥被轉開時,會突然很想喝上這樣一杯,明知其實無香氣可言、充滿糖份與不好代謝的反式脂肪,對身體無所益處的即溶咖啡。
取來很小的杯子,倒入七分滿的粉末,極濃郁的泡上一杯;感受一團不自然的甜味流入體內,那些化不開的白色奶精懸浮的是國高中時期蒼白的記憶:清晨六點矇昧的校車、無止盡的考試、與父親的爭執,全都一圈又一圈旋轉着。貝納頌、三十六法郎、輕鬆小站,甚至是老牌伯朗,皆陪我度過了那些去市立圖書館的日子。像是體內有了另一個以咖啡築起的沙丘,在每個凹痕中支撐着我不倒、不會就此沉沉睡去。
咖啡是抗衡、戰爭、有所求。心有所住的漆黑。
漆黑之中,我看見自己的軀殼變形,渴望遊着便能遇見螢光珊瑚,靠近舞動着婀娜觸手的章魚,渴求旖旎的海妖之歌,浪與浪的交疊之際,飄散出花果酒香。
啪啦一聲,熱水沸騰了,我一下子回到桌前。水溫九十,穩住手臂的力量,衝濾紙、在拍平的咖啡粉上悶蒸、繞圈,空氣被推擠出來,在粉的表層吐出泡泡,像是要說些什麼。
想像着這杯咖啡該有的香氣,葡萄、野薑花、紅糖、檸檬,我知道自己在往後的人生仍會一杯又一杯的喝下,爲的不是清晰的腦袋,而是那隨着顆粒粗細、水溫高低而變幻莫測的香氣,爲了在血液裡注入熱烈的咖啡因,如在體內燃火,小小的巫師們手拉手圍成圈,在生活裡執下迷幻草藥。
我會一遍又一遍的喝下,無論是帶點透明的琥珀色、深黑色、淺褐、濁黃,讓所有血管通紅,如若點燈,有燈的地方有人,便有或明或暗,酸甜不一的慾望。












